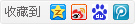电话:0592-2048015 传真:0592-8127339 邮箱:tpys_0592@qq.com 微信号:taipingyansi

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涉及宗教(尤其是世界性宗教)敏感的挑衅、攻击性报道,往往会容易引发冲突甚至暴力对抗。背后每每体现出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即:在西方被广泛定义为“言论自由”的媒体行为,其以无神论、世俗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理念并不被非西方以及重视宗教神圣性、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完全认可,最突出体现在以“言论自由”为名而出现的对宗教无底线的攻讦。言论自由的精神具有普适性,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言论自由的具体模式又是基于具体历史过程形成的一种“地方性伦理”,它是有边界的,它的部分观念并不真正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全球化时代,人类正在从千姿百态的舟船登上一条同舟共济的大船,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在媒体伦理的传播、认同过程中,还不能忘记重构的时代使命。各种文明都要学习尊重“他者”的文化价值,从法律上设立言论自由的边界,尤其要约束无底线的言论自由的挑衅性言论;同时,也要考虑在世俗社会中,给不同信仰的“神圣”领域留出一片天空。
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某一地域媒体的新闻报道引起的纠纷,往往能迅速蔓延以至于演变为国际性冲突。当涉及宗教(尤其是世界性宗教)的敏感问题时,尤其如此。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多起此类重大事件。例如: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间的“丹麦漫画”事件,2012年9月的《穆斯林的无知》事件,2015年1月的《查理周刊》事件等。它们往往由西方媒体刊载伊斯兰教敏感内容引发,然后,迅速演变为多国范围的暴力冲突。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甚至有升级为不同文明对抗的趋向。
毫无疑义,任何暴恐行为均应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然而如果深究则会发现,冲突的根由多源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的矛盾累积,而媒体恰恰又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在传播全球化时代,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媒体又当如何思考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以及对待“挑衅性言论”?如何对待“他者”的“神圣”地带?这些已经成为当下媒体伦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媒体伦理的文化冲突:自由还是亵渎
媒体伦理是媒体所应秉持的道德价值取向,它是社会对媒体角色的应然要求,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在传播领域的体现。在近年来新闻报道引起的冲突中,西方社会和那些重视神圣性、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各自的媒体伦理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价值冲突。
西方的立场,从他们的一系列反应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2006年“丹麦漫画”事件时,他们在优先维护“言论自由”上就表现出高度一致。2006年1月6日,丹麦地方检察官以言论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为由,免于起诉《日德兰邮报》;2月16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声明:伊斯兰世界有权利和平抗议,但言论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审查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报纸也正是以“言论自由”为名转载漫画的。当时,法国《法兰西晚报》还发表评论文章《是的,我们有权丑化上帝》。该报总编勒夫郎也说:“世俗社会中没有‘宗教教条’的地位,这也是我们重新发表这些漫画的初衷。”
同样,《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法国社会虽然在是否继续刊登穆罕默德漫画上产生分歧,但均认为媒体有亵渎宗教的权利。1月13日,法国总理瓦尔斯“坚称‘亵渎神明’从来不是法国法律中的条款,也永远不会。”法国资深媒体人、《国际邮报》亚洲部主任Agnès Gaudu虽然并不接受《查理周刊》的做法,但他还是认为:“这是法国传统的一部分。”法国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在西方,“无论英、美、法、德哪一个国家,在反对传统教权、反对迷信与宗教非理性的偏见和狭隘方面是有共性的”。
在欧美大多数国家,亵渎宗教言论的确是受到宪法或法律保护的。以美国为例,“一般而言,在报纸上刊登、在电台中播出或者在墙上和篱笆上书写此种恶言谩骂的人受到宪法保护”。2012年,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起风波。当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解释说,美国尊重信仰自由,但不禁止亵渎他们最为神圣的信仰的言论。
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在那里,宗教的神圣性是不容亵渎的。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和政治、社会、文化等相互交织,即使是所谓世俗国家,传统教法也有巨大的约束力。譬如,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态度非常独特,既不允许侮辱诽谤,又不允许加以神化。不允许为其画像、造像,更禁止张贴和悬挂他的任何图像,即使是赞美性的。漫画这种表现形式则被认为是亵渎和挑衅。这是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也影响着他们的情感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
同时,“亵渎在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均为犯罪,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比如在巴基斯坦,该国《宪法》和《刑法》中均有相关规定。该国《刑法》第298条规定:“不论任何人,在他人能够听到或看到的范围内说出任何故意伤害他人宗教感情的话,或做出故意伤害他人宗教感情的动作,或放置故意伤害他人宗教感情的物品,都应处以一年以下监禁或罚款,或二刑并罚。”土耳其、埃及等世俗穆斯林国家,也均有对亵渎行为的立法约束。
在佛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度,也有关于亵渎宗教言论的法律规制。根据青年学者卢家银的研究,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都用立法的方式禁止侮辱宗教领袖、扭曲宗教教义和嘲弄宗教习俗;对于亵渎宗教的言论,一般会给予较轻的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3个国家还对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提供同等保护。2006年5月,电影《达芬奇密码》事件中,应斯里兰卡天主教会的请求,斯里兰卡禁止了该片在当地影院上映和在当地电视台播出。
禁止亵渎宗教是许多非西方以及重视宗教神圣性的国家或族群的伦理共识。只要“禁止”建立在充分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基础上,就应该承认这是为达成社会和谐所作的必要限制,它在文明内部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普遍性知识其实多由“地方性知识”转化而来的理论,与视西方亵渎宗教为正当的“普遍性知识”相较,为什么禁止亵渎宗教的理论就不可以从“地方性伦理”转化为“普遍性知识”?
就本文而言,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显然是在适用标准各异的媒体伦理。一些在西方被广泛定义为“言论自由”的媒体行为,在非西方以及重视宗教神圣性、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中,不但不能得到认可,还被视为实实在在的亵渎与恶意挑衅。因此,有学者称,“宗教领域的冲突与和谐、论战与对话,近乎一个无法梳理开来的死结。”
■“地方性伦理”反思:警惕傲慢与偏执
在一系列冲突中,确曾出现过一些穆斯林的过激甚至极端行为,然而更不乏西方主流社会的傲慢与偏执。对广大穆斯林来讲,对穆罕默德的亵渎就是对穆斯林群体的侮辱。冲突发生初期,穆斯林群体往往通过和平抗议和示威,合理表达要求得到理解与尊重的诉求。然而,由于偏执于“宗教亵渎自由”,伊斯兰世界的声音每每被西方社会和媒体有意无意地忽视、回避,甚至是误读、曲解。西方社会后续的一些不理智行为,成为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丹麦漫画”事件中,《日德兰邮报》主编于2006年1月31日公开道歉,冲突本将趋于缓和。第二天,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报纸却又转载肇事漫画,《法兰西晚报》更在头版刊登一则新漫画,讽刺四大宗教的神。2月3日,《日德兰邮报》发表社论,再次道歉;2月8日,法国《查理周刊》又刊出肇事漫画,更在一幅新作品中讽刺穆罕默德为“白痴”。西方诸多媒体的这一系列以“言论自由”为名的行为,正是“宗教亵渎自由”理念的产物。冲突发生后,媒体本应倾听“他者”的声音,致力于事件平息,西方媒体却一味坚持己见,使冲突的范围和程度进一步扩大,这是不够理性的。
同一事件中,2005年10月19日,11位伊斯兰国家驻丹麦大使约见丹麦首相,“希望他与《日德兰邮报》刊登的漫画,以及丹麦媒体上其他对伊斯兰教不友善的言论保持距离。”而丹麦首相则以言论自由不得干涉为由谢绝会见。丹麦首相的态度无疑对事件的发展给予了负面影响。
在其他媒体引发的冲突中,也能够看到类似情景。1988年至1989年的《撒旦诗篇》事件中,“穆斯林虽然感到受了伤害,但最初并没有激烈举动,只是要求作者和出版商在书中添一插页,声明该书故事纯属虚构,所涉及的伊斯兰历史并不准确。但作者和出版商都没有认真对待此事,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一部书可以伤害一群人,可能导致一群人过激行为的发生。”还有,在《查理周刊》事件中,2015年1月14日,《查理周刊》出版新一期杂志,仍以穆罕默德漫画为封面。正是这新一期杂志,引起了伊朗、埃及等诸多伊斯兰国家民众的抗议,进而演变为新的暴力冲突。
其实,言论自由的核心精神固然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其具体做法和界限则是与国家、民族、文明的历史传统紧密相关的,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地方性伦理”。上世纪70年代,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认为一切知识均不具有脱离文化背景的绝对正确性特征。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家们“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反过来观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终于意识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原来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西方亵渎宗教的自由正是在反天主教教权的历史中形成的,你压制科学、迫害科学家,我就从根本上嘲笑你、攻击你、否定你,这就形成了你来我往的对立和冲突。在法国,世俗社会的确立过程,正是天主教不断受到质疑、批判、讨伐,从而从世俗社会逐步退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和文学家们对它教义中的矛盾和荒谬极尽嘲讽。由于受到言论自由的持续冲击与挑战,天主教最终被迫放弃对世俗政治的介入。“在被嘲讽500多年后,天主教最终‘被庸俗化’”。但此种压制科学、迫害科学家的情形在伊斯兰教中并没有出现过,所以敌意就显得毫无来由。因为敌意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范围和特定的背景,它是欧美世俗社会的产物,所以并不具有跨文明的约束力。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狭隘性日益充分地体现出来。
在西方其他国家,宗教也大都经历了类似过程。世俗化以后的宗教几乎完全退出了公共领域,退缩到纯粹的个人空间中去。所以,西方大都形成了自由亵渎宗教的现实并成为普遍接受的媒体伦理。当冲突发生时,他们往往优先保障言论自由,认为这“给我们关于表达自由的定义增添了实质的确定性。”
基于世俗主义、无神论哲学基础的西方新闻自由标准,在特定文明内部有较强的适用性,但作为一种“地方性伦理”,它的部分观念并不具有充分的跨文化的普适性,当它推展到非西方以及重视宗教神圣性、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与族群中时,尤其如此。因为一旦跨越边界,“自由或言论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实质性的历史条件和法律保护就会发生致命的位移。”这时,倘若自视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并要求其他文明必须接受,就可能引发强烈冲突,其行为也就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文化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偏执。
在全球化时代,族群生存已经超越了地域性局限。在世界已经相互联系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时,跨文化传播中,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异、真诚地倾听“他者”的诉求、给“他者”以应有的空间,往往比“理直气壮”地自说自话更为重要,也更有利于族群和谐。因此,西方政要及诸多媒体在《查理周刊》等事件中,每每以世界文明表率自居,却又轻率地伤害“他者”宗教情感的行为,是需要有所反思的。
■媒体伦理的重构:尊重“他者”文明与禁止挑衅
以全球化视野来审视,不管是西方世界还是伊斯兰世界,两者的媒体伦理都是地域性的。当它们发生冲突时,让一种媒体伦理完全屈从于另一种是没有必然理由的。但是,只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看问题,必然会缺少对“他者”文明的必要同情和理解。比如,欧美人喜欢对包括父辈在内的人直呼其名,但中国人恐怕难以接受自己的孩子如此效仿。所以,用自己的合理性来破坏他人的合理性,就容易先入为主。以自身的标准去要求“他者”,就必然表现出傲慢、固执、狭隘与偏见等,容易引发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团体的冲突。冲突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族群关系的撕裂,往往难以轻易补救。长此以往,将可能造成更为重大的世界动荡。这正是社会有识之士所担忧的。
重构跨文化的媒体伦理,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重构的根本途径就是“对话”。这就需要各方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承认“他者”文明的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需要“参与共建的各方没有谁具有绝对的精神及道德的优越性,并且各方承诺放弃暴力的对抗和挑衅性的行为。之后,通过协商、讨论、辩论来表达抗议或申明正当性。”而处于强势一方的文明,更有责任首先检视自己的言行。
其实,在美国,早就有过对挑衅性言论的思考。在1942年的查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弗兰克·墨菲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判决意见里概括了“挑衅性言论原则”。他认为挑衅性言论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内,原因就在于:“挑衅性言论——那些言论的发表会造成伤害或可能引发对和平的直接破坏。人们已经清楚地觉察到,此种言论不是任何思想探索的本质所在。作为通向真理的阶梯,它们仅具有微乎其微的价值,秩序与道德方面的社会利益显然要大于它们所能带来的所有好处。”
这一原则可以化解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具体措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建构,有时可以借助立法推行,有时可以通过媒体自律实现。在西方国家,媒体自律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在2006年“丹麦漫画”事件和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中,美国主流媒体表现出相当的谨慎和克制。《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马蒂·巴龙解释说,决定不刊登批评伊斯兰教的漫画是因为他的报纸‘不刊登任何挑逗性、有意识或者不必要地伤害宗教群体的内容’”。“《纽约时报》透露说,如果存在‘伤害宗教敏感’的意图,‘通常’毫无可能刊登。”澳大利亚的一些主流媒体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它们的做法,可以为未来提供有益的借鉴。
限制挑衅性言论原则,同样可以指导其他不同文明体系之间言论自由边界的界定。言论自由不仅要尊重宗教信仰,也应该尊重世俗社会的禁忌。学人吴钩在《如果宋朝有<查理周刊>,悲剧会发生吗?》一文中说,“每个时代都有言论的禁忌,这些禁忌通常被排除在言论自由的边界之外。”这里涉及到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待“他者”诸“神”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文化体系或族群的禁忌,涉及的都是整个族群的“信仰”问题,这是他们的“神”或“神系”。或许是超自然的存在,也或许是一系列世俗的英雄谱系,但这些“神”是维系文明价值体系的关键,是一个族群的象征与心灵家园的守护者。对他们来讲,这是神圣而不容亵渎的。自然,这也应该成为媒体伦理中不可碰触的底线。
最后,还需要明确一点。媒体伦理重构要约束挑衅性言论,不是言论自由向宗教与禁忌屈服,而是在全球化时代,为了人类的和平,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言论自由”重新建构,剔除其殖民主义与工业化时代的狭隘,赋予其适应时代的内涵,权衡利弊作出的必要抉择。约束挑衅性言论,不应伤及言论自由的底线。要严格界定挑衅性言论的范围,保障对宗教与禁忌自由而公正的讨论。因此,“信仰”自身也需要作出调整和让步。学者许纪霖认为:“世俗对宗教可以有批评、有研究、有讨论,但不能用无聊的亵渎冒犯他者。”(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号:闽(2022)0000011 闽ICP备19021265号-1
电话:0592-2048015 邮箱:tpys_0592@qq.com 微信号:taipingyansi
Copyright 2010-2025 太平岩寺 All Rights Reserved.